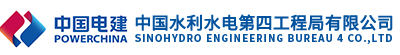折疊的時(shí)光 |
|
|
|
|
今年冬至的餃子,包得有些不同。食堂里早備好了兩大盆餡兒,一盆是北方經(jīng)典的韭菜豬肉,肥瘦相間的肉糜裹著斬得細(xì)碎的青葉子;另一盆是韭黃雞蛋,金燦燦的顏色里透著家常的親切。面是食堂大師傅提前和好的,一摞摞擱在案板上,用濕紗布蓋著,怕被壩上這干烈的風(fēng)吹皴了皮。空氣里浮動(dòng)著蔥姜的辛香、麻油的醇厚,還有面粉那踏踏實(shí)實(shí)的、微微發(fā)甜的氣息。這氣息像一條溫暖的河,一下子就把人裹了進(jìn)去。 我的手指觸到那微涼而柔軟的餃子面時(shí),心里那點(diǎn)“說(shuō)不上來(lái)的感覺(jué)”,忽然就找到了一個(gè)著力點(diǎn)。三年了,同樣的冬日,同樣的活動(dòng),手指的記憶卻比心思來(lái)得更直接。不用看,拇指與食指便自然地尋到那面皮的邊緣,一捏兩折三折四折,一個(gè)敦實(shí)實(shí)的麥穗餃便立在掌心了。這手藝,還是第一年冬至?xí)r,跟著生產(chǎn)部的小麻姐姐學(xué)的。她是青海姑娘,手巧得很,褶子勻稱得像用尺子量過(guò)。她那時(shí)一邊包,一邊用青海話說(shuō)著:“冬至不吃餃子,耳朵要凍掉哩!”哄堂的笑聲,仿佛還能聽見余音,可一抬頭,原來(lái)她坐著的位置上,正坐著個(gè)眉眼尚帶些學(xué)生氣的年輕人,正笨拙地試圖把裂開的餃子皮捏攏,鼻尖上還沾了點(diǎn)兒面粉。 這便是那“新面孔”了。他們眼里有著我們當(dāng)年一樣的、新鮮而略帶茫然的光,好奇地打量著周圍的一切,問(wèn)著“這個(gè)閥門往左是開嗎”“圖紙上這個(gè)標(biāo)高是不是有誤”之類我們?cè)?jīng)也問(wèn)過(guò)的問(wèn)題。而我們這些“老人”,三年的時(shí)間,說(shuō)長(zhǎng)不長(zhǎng),說(shuō)起初離校門的青澀,卻已足夠磨去一層。皮膚糙了,嗓門大了,走路的步子也踏得更實(shí),更慣于在機(jī)器的轟鳴里扯著嗓子說(shuō)話,在寒風(fēng)里就著灰土咽下盒飯。我們成了他們口中的“師傅”,成了知道庫(kù)區(qū)哪個(gè)角落背風(fēng)、曉得拌合站老師傅最愛抽什么煙的人。這身份的轉(zhuǎn)換,起初是不自知的,直到在這樣的場(chǎng)合,看著他們,才恍然驚覺(jué)——原來(lái)那條名為“青春”的河,我們已經(jīng)涉過(guò)了一段不短的水程。河岸的風(fēng)景變了,我們的倒影,也不再是當(dāng)初的模樣。 我的目光不由得飄向窗外。透過(guò)蒙著水汽的玻璃,越過(guò)食堂前那片壓著霜的空地,便能望見我們親手“堆”起的“山河”。那座電站,就沉默而巍然地矗立在冬日的天幕下。三年前的冬至,我第一次參加這活動(dòng)時(shí),窗外還是一片莽蒼。只有勘探時(shí)立下的紅色小旗,在無(wú)遮無(wú)攔的野風(fēng)里孤零零地飄著,遠(yuǎn)處是鐵青色的山脊線,像大地沉默的骨骼。我們包著餃子,聊的是即將開挖的基坑有多深,截流的龍口該怎么安排。那時(shí)心里揣著的,是一張宏偉卻冰冷的藍(lán)圖,是對(duì)未知工程的興奮與忐忑。餃子吃在嘴里,味道是滾燙的,心思卻飄在寒風(fēng)呼嘯的曠野上。 第二年,窗外已是大不同的景象。壩體的雛形已經(jīng)起來(lái),巨大的混凝土墻體像從大地深處生長(zhǎng)出的灰色堡壘,起重機(jī)巨臂林立,車輛穿梭如蟻。包餃子時(shí),手上沾著面粉,嘴里聊的已是澆筑的溫控、灌漿的壓力。那次的餃子餡好像咸了些,大伙兒一邊喝水一邊笑罵,可看著窗外那日益成型的龐然大物,心里頭是滿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摹⒖煲绯鰜?lái)的成就感。那是一種創(chuàng)造者的、近乎父親看著孩子一天天長(zhǎng)大的滿足與焦灼。 而此刻,窗外的一切都沉靜下來(lái)了。主體工程已然完工,電站像一頭休憩的巨獸,安靜地伏在山谷之間。它的線條是那樣硬朗而流暢,在冬日稀薄的陽(yáng)光下,泛著混凝土特有的、堅(jiān)實(shí)的光澤。沒(méi)有穿梭的車輛,沒(méi)有鼎沸的人聲,只有它本身,帶著一種完成使命后的、莊嚴(yán)的寂靜。三年,從無(wú)到有,從荒蕪到矗立,一千多個(gè)日夜里,我們的青春、汗水、爭(zhēng)執(zhí)、歡欣,仿佛都被攪拌進(jìn)了那成千上萬(wàn)噸的混凝土里,澆鑄成了這沉默山體的一部分。它不再只是圖紙上的線條,報(bào)表上的數(shù)字,它是我們生命中被開鑿出的一段峽谷,一條我們自己用歲月匯成的、更為沉靜的河流。 鍋里的水第三次沸騰了,白色的蒸汽洶涌地頂起鍋蓋,食堂里彌漫開煮熟面皮與餡料融合的、令人心安到幾乎鼻酸的豐腴香氣。第一盤餃子出鍋了,白胖胖、熱騰騰地堆在盤里,薄皮隱隱透出內(nèi)里餡料的顏色。大伙兒一擁而上,笑聲、筷子的碰撞聲、被燙到的吸氣聲,瞬間鬧成一片。我也夾起一個(gè),蘸了點(diǎn)陳醋,送入口中。面皮的柔韌,餡料的鮮香,汁水的滾燙,一下子在舌尖炸開。這味道,與第一年、第二年,似乎并無(wú)不同,可咽下去,那暖意一路氤氳到胃里,再慢慢擴(kuò)散到四肢百骸時(shí),卻品出些更深的東西來(lái)。 那不只是食物帶來(lái)的溫暖,是在這遠(yuǎn)離故土的僻遠(yuǎn)之地,一群原本陌生的人,因一項(xiàng)共同的事業(yè)而聚攏,在古老的節(jié)令里,用最樸素的方式,彼此確認(rèn)著溫度,確認(rèn)著“在一起”的踏實(shí)。這餃子里,包進(jìn)去的是韭菜豬肉,是韭黃雞蛋,又何嘗不是這三年的寒來(lái)暑往,風(fēng)霜雨雪,是那些想家的夜,攻堅(jiān)的關(guān),還有此刻身邊這些熟悉或正在變得熟悉的面孔?我們吃下的,是一段共同澆筑的時(shí)光。 窗外的電站依舊沉默。但我知道,當(dāng)來(lái)年春汛涌動(dòng),山間的積雪融化,萬(wàn)千細(xì)流匯入這我們親手打造的容器時(shí),它將不再沉默。它將開始低吟,開始轟鳴,將沉睡了千萬(wàn)年的水的力量,轉(zhuǎn)化為照亮遠(yuǎn)方城市的光與熱。我們的河流,將以另一種形態(tài),開始它永恒的奔流。 而我們的河流呢?電站建成了,一些人會(huì)留下,更多的人,或許像很多已經(jīng)離開的人一樣,奔赴下一個(gè)“尚義”,在另一片荒蕪上,再次開始從無(wú)到有的創(chuàng)造。這或許就是工程人的命運(yùn),也是工程人青春的特質(zhì)——我們永遠(yuǎn)在建造“完成”,自己卻永遠(yuǎn)在“路上”。但有什么關(guān)系呢?我們?cè)诖颂帲瑢⑶啻簲Q成鋼筋,將歲月夯為壩體,我們創(chuàng)造了一條能發(fā)電的、物質(zhì)的河;而我們每個(gè)人,也從此成了一條河,身上帶著“尚義”這一段峽谷的深刻地形,帶著混凝土的堅(jiān)定與餃子的溫?zé)幔^續(xù)向著生活的、事業(yè)的下游,不舍晝夜地流去。 盤子里的餃子漸漸見了底,身上的寒意早已驅(qū)散。我喝下最后一口餃子湯,那原湯化原食的暖意,通達(dá)而舒暢。天,已經(jīng)黑了。但明天,太陽(yáng)會(huì)照常升起,照在電站嶄新的閘門上,也照在我們即將踏上的、各自的新征程上。 那條河,在餃子的褶皺里,在我們生命的河床里,正浩浩湯湯,流向燈火斑斕的遠(yuǎn)方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(guān)閉】 |